【大家】
作者:葛承雍(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、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)
蔡鸿生先生的名气,不如他的学问那么大。在学术界,“蔡鸿生”这个名字,并非玉落大海、默默无闻,也算不上如雷贯耳、声震八方,但在我看来,他是一位真正的“大先生”。
何谓“大先生”?在汉语中,“先生”是一个尊称,“大先生”更是对人格、品德、学业上能为人表率者的尊称,只有社会的尊者、育人的能者、心怀家国学问的大者,方可称为“大先生”。蔡鸿生先生就是这样的“大先生”。他一生行事低调,远离平庸,他的求真思索可以使后学受益终生,他的求新成果经得起历史的长久推敲,多年以后依然可以在浩瀚书海里熠熠生辉。

文章插图
学人小传
蔡鸿生(1933—2021),广东汕头人,历史学家。1953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学专业,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。曾任该校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、《历史大观园》月刊主编。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,重点探讨唐代粟特、突厥文化,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,岭南佛门僧尼史事,广州与海洋文明,历史研究的学理和方法等领域。著有《俄罗斯馆纪事》《尼姑谭》《清初岭南佛门事略》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《广州海事录: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》等。
我不是蔡鸿生先生的亲炙弟子,顶多是个私淑弟子,但是我对他的敬仰不亚于入室弟子。“文革”前,蔡先生30岁出头,就在《历史研究》等杂志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。那时发表论文的机会很少,比今天难得多,他不仅发表了,而且其独到的见解受到学术界重视。20世纪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,曾仔细拜读过他的论文,知道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,从中古突厥到近代广州,从中西交通到海丝港口,融会贯通,由博返约,在见面之前,就已经对他非常敬重了。
1996年我去广州开会,在中山大学第一次拜见蔡先生,那时他63岁,满头鹤发,白眉低垂,精神矍铄,很像一尊参透了世间万象的神。那次,蔡先生亲自带我去了陈寅恪的故居,还讲了一些他自己读书时的情况。1953年秋,他20岁,跨进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门槛。1955年,以“元白诗证史”选修生的身份听陈寅恪先生讲课。授课是在陈寅恪家里,正式的选修生加上旁听的教师,一共只有几个人。陈先生讲学很有魅力,借历史、文学揭示古代社会与人性的冲突,由表到里启发学生理解历史,令人茅塞顿开。
如今,距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20多年了,蔡先生也已经去世整整一年了,但我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,不由感到,要在新的环境下重新体会老一辈“大先生”的风神气韵,回望他们作为真正的学术耕耘者的心路历程。
【 大先生|他的胸中有世界——一个编外学生对蔡鸿生先生的纪念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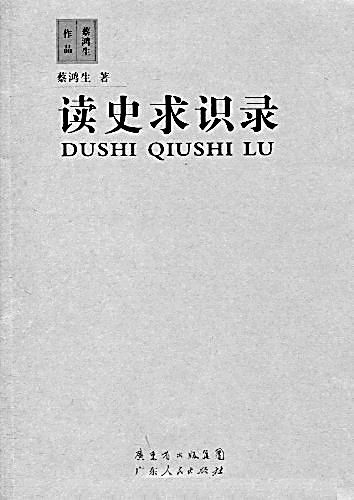
文章插图
《读史求识录》
没有毕业,只有毕生
蔡先生上大学时,受到过严格的思辨能力训练,陈寅恪等老先生传授的史学思维又给他的读书实践增添了许多养料。他多次和我聊起马克思、费尔巴哈等西方哲人的著述,也谈起陈寅恪、岑仲勉等人的学术贡献,这与他五六十年代的学习背景有关。那时的理论学习,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,也为他奠定了站得高、看得远、走得长的学术基础,因此才能在日后纵横古今、联通中西。
他也要求我读一些西方历史哲学著作,尤其是那些历史哲学、宗教批判的经典。这些书对人类的思想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,不仅是学术经典,而且是如今我们理解西方社会基本观念的重要基础。遗憾的是,这些书我读过就忘记了,只了解了皮毛,没能吸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。
20世纪60年代,蔡先生还是一个青年教师时,就已经具有环视世界的眼光和胆识了。他游走在“西洋”与“西域”之间,发表了多篇引起学界关注的高质量论文,后来又以突厥和九姓胡的研究名满学界。他虽然成名很早,但始终执着于学术,淡泊名利,以一介书生的力量,播撒智慧,收获果实。
蔡先生非常重视学术传统的传承。他说:“一个学科需要几代人努力,陈寅恪、岑仲勉这样中山大学‘双星’的班现在谁来接?过去,很多人不知道丝绸之路是什么,现在人人皆知。但唐宋丝路与明清丝路不同,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丝绸的输出与历史上的丝绸贸易也是不一样的。地理大发现后,资本主义的贸易与以前的贸易大不一样,广州十三行也变成了丝绸之路贸易,走西口的也成了丝绸之路贸易。不懂这些,研究就走样了。这就是陈寅恪讲的‘要有通识’。”
- 杜运燮|《西南联大现代诗钞》:一本书,一所名校,一个诗派
- 中共一大纪念馆|“伟大建党精神专题展”开启全国巡展!
- 正定|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公布 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入选
- 专家们|殷墟大墓曾出土一个鼍鼓,古人制鼓为何不去甲片,让人至今想不通
- 清华大学|美术馆嵌入产业园,上海打开“科创+文创”新模式
- 肯德基|00后大学生的「职业代吃」江湖:重新定义“吃软不吃硬”
- 九楼四塔八大寺|游丹青长卷 寻正定胜迹
- 国字山|江西樟树国字山战国墓葬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
- 考古学|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,呈四大特点
-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,20个项目入围
